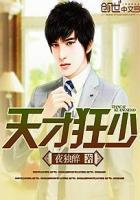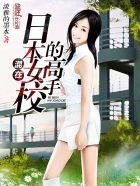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华娱之摄影系大导精校版 > 第724章 乌合之众(第2页)
第724章 乌合之众(第2页)
“因为你二十年前拍《边缘地带》的时候,我在北电图书馆看了七遍。”姜闻轻声道,“那时候我就想,总有一天,我也要拍出让人不敢删的电影。”
挂了电话,王泉安站在阳台上久久未动。
远处城市灯火连成一片,像一片永不熄灭的星海。他忽然想起二十岁那年,在山西矿区蹲点三个月,只为捕捉矿工下班后那一瞬的沉默。那时他相信,只要诚实地记录,总会有人懂。
如今他老了,头发花白,膝盖因长期蹲守落下了风湿,可那份信念竟在这一刻重新燃起。
第二天傍晚,北海公园湖面结着薄冰,仿膳包间临水而设。吴宸早已等候多时,一身藏青色中山装,神情沉稳。
两人寒暄落座,服务员端上宫廷点心。酒未开,话先起。
“你的片子我看了。”吴宸开门见山,“技术扎实,情绪克制,文学性强。问题是??太狠了。”
“哪一点狠?”王泉安直视对方眼睛。
“矿难瞒报那段,原型是谁?辽源?鹤岗?还是大同?”
“艺术源于生活,但不对应具体事件。”王泉安答得谨慎。
“可观众会联想。”吴宸摇头,“你知道总局最近定调吗?‘主旋律要温暖人心,现实题材也要传递希望’。你这个结尾,父亲死了,儿子走了,工厂塌了,整座城像座坟墓。这不是希望,是绝望。”
“可那就是现实。”王泉安声音提高,“那些人真的死了,那些厂真的倒了,那些家庭真的破碎了!我们拍电影,难道就是为了造梦?”
“梦有时候比现实更重要。”吴宸缓缓道,“你要真想让它活下来,就得学会戴着镣铐跳舞。”
王泉安冷笑:“所以我得加个光明尾巴?比如儿子回来带头创业,振兴家乡?”
“不一定非得创业。”吴宸喝了口茶,“你可以让他寄一封信回来,信里写:‘爸,我在这座废墟里看到了新的可能。’一句话就够了,既保留批判性,又留了光。”
王泉安沉默良久。
他知道,这已经是极限的让步。
就在他准备开口答应时,手机震了一下。
微信弹出一条新消息,来自姜闻:
【我把《锈河》推上了“亚洲新声”初评名单。评审团尊重原创完整性,不会要求修改。只要你愿意,下周就能送审柏林。】
他抬头看向吴宸,忽然笑了。
“吴老师,谢谢您这顿饭。但我决定??不改了。”
吴宸眉头微皱,“你确定?现在撤还来得及。一旦走国际路线,国内上映基本无望。”
“或许吧。”王泉安站起身,语气坚定,“但如果连真实都不敢呈现,我还当什么导演?宁浩能拍《疯狂的石头》,陈凯哥能熬过十年沉寂,姜闻敢在柏林提议设立‘亚洲新声’,他们都在往前冲。我不能往后退。”
说完,他转身离去,脚步稳健。
包间里只剩吴宸一人,望着窗外渐暗的湖面,轻轻叹了口气。
他知道,这个时代变了。
过去是他掌握审批权,决定谁可以上岸;而现在,有人已经绕开堤坝,直接驶向大海。
三天后,《锈河》正式提交柏林电影节“亚洲新声”单元评选。
与此同时,姜闻在北京电影学院主持了一场闭门研讨会,主题为“审查与表达:中国导演的生存策略”。
到场者包括宁浩、乌尔善、曹保平、娄烨,以及几位从未公开露面的独立制片人。
会议持续六小时,全程录像加密存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