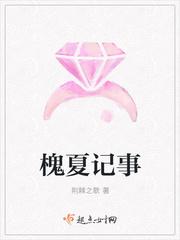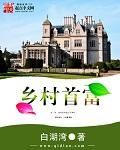笔趣阁>华娱之摄影系大导精校版 > 第725章 投了名单(第1页)
第725章 投了名单(第1页)
京城的媒体,从不缺头条。
第二天一早,吴宸、刘伊菲、张艺某和贝尔和四人私下聚餐的新闻,就登上了各大娱乐版的版面。
照片拍得有些模糊,显然是偷拍的,但四人的轮廓清晰可辨。
新闻稿写得倒。。。
柏林电影节进入第七天,《锈河》在“亚洲新声”单元的首映安排在晚间七点,电影宫二号厅。放映前两小时,门口已排起长龙,许多观众举着中文标语牌,上面写着“真实即力量”“我们看见了锈河”。场刊记者注意到,其中不少是来自德国、法国、日本的年轻影评人,他们提前读过样片介绍,专程赶来。
王泉安没有出现在红毯上。他坐在北京家中,电脑屏幕分割成四个窗口:一个是直播信号源,一个是弹幕池,一个是海外社交平台实时评论流,最后一个,是姜闻发来的视频通话邀请。
“别紧张。”姜闻的声音透过耳机传来,“评审团全员到场,包括去年戛纳金棕榈得主玛雅?杜尔。她说看了《锈河》的矿工抗议段落,整整一夜没睡。”
王泉安点点头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边缘。那杯子是他父亲留下的,搪瓷剥落,印着“先进生产者”五个红字。他曾把它用作道具,在影片第五十分钟父亲砸办公室的戏里,那杯子从桌上滚落,碎了一地。
直播画面切换到影院内部。灯光渐暗,银幕亮起,胶片特有的颗粒感在高清投影下愈发清晰。第一个镜头是雪地里的铁轨,延伸向灰蒙蒙的天际,远处烟囱冒着黑烟,像垂死巨兽的呼吸。
弹幕开始滚动。
【这质感……十年没见过了】
【开场三分钟,我已经哭了】
【这不是电影,这是历史档案】
当第三十八分钟矿工集体下跪的画面出现时,现场响起轻微抽泣声。一名德国女观众摘下眼镜擦拭眼角,身旁同伴轻拍她的肩膀。而在北京的王泉安,闭上了眼睛。他知道这一段曾被审查组批为“制造对立”,要求彻底删除。但他坚持保留??不是为了煽动,而是为了让那些沉默的人,至少能在光影中跪一次。
第五十六分钟,父亲怒砸厂长办公室,玻璃碎裂声刺耳而真实。这个镜头实际拍摄时用了真玻璃,群演中有一人被划伤送医。当时制片主任劝他重拍,用道具玻璃加音效合成。他拒绝了。“痛就该有声音,”他说,“不然观众怎么听得见?”
此刻,柏林现场爆发出一阵掌声。不是结束后的礼节性鼓掌,而是中途的情绪释放。有人高喊了一句德语,翻译软件迅速识别出:“这才是电影!”
姜闻坐在第一排,微微侧头看向身边的评审团成员。他看到法国导演洛朗?贝尔点头,意大利女制片人眼含泪光,美国纪录片大师约翰?克莱恩甚至掏出笔记本记下了什么。他知道,这一刻的意义早已超越一部影片的成败。
放映结束,全场起立鼓掌。持续六分钟,掌声未歇。有记者数了,这是本届电影节至今最长的一次中场致意。
后台休息室,王泉安终于接通了现场视频。姜闻走进来,脸上带着少见的激动:“评审团要求加映一场,明天中午。还有三家欧洲发行商想谈版权,其中一家是荷兰的VPRO电视台,他们说要把《锈河》放进‘人类困境影像计划’永久收藏。”
王泉安嘴唇颤抖,说不出话。
“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?”姜闻笑了笑,“刚才文化参赞打来电话,说国内宣传口正在开会,讨论要不要把《锈河》纳入‘一带一路’文化交流项目。”
两人相视片刻,忽然笑出声。
笑声还未落定,手机震动。是宁浩发来的微信语音。
“老王,刚看完直播。”宁浩声音低沉,“我他妈后悔了。十年前你说让我别改《疯狂的石头》结局,我没听,加了个警察破案的大团圆。现在想想,要是当初狠一点,也许今天站柏林台上的就不只是你一个。”
王泉安回了一句:“你现在也不晚。”
第二天,《锈河》登上《银幕》《综艺》《卫报》等主流媒体影评版头条。《好莱坞报道者》称其为“本世纪最锋利的华语现实主义作品之一”,并特别提到:“它没有控诉,却让控诉无处不在;它不提供答案,但每一个问题都刻骨铭心。”
与此同时,国内八城艺术院线开启限量公映。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凌晨三点就有人排队购票,黄牛将票价炒至八百元一张。上海UME国际影城临时加开三场,仍一票难求。广州一位退休教师带着全家三代七口人观影,散场后在微博写道:“这片子让我想起九十年代下岗潮,那时候没人敢说,现在终于有人说出来了。”
更令人意外的是,抖音和快手平台上,一段“《锈河》真实原型探访”短视频悄然走红。博主是一名东北大学生,寒假返乡时走访了影片取景地附近的废弃钢厂,拍摄了仍在拾荒的老工人、结冰的家属区水管、墙上斑驳的“安全生产”标语。视频配乐是电影原声中的口琴曲,哀而不伤。